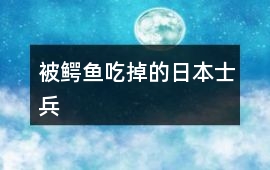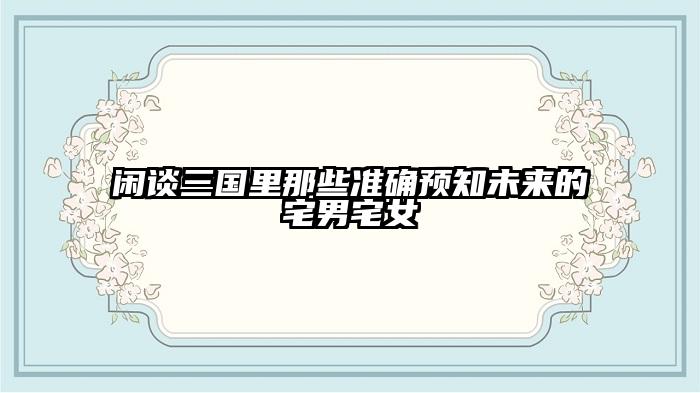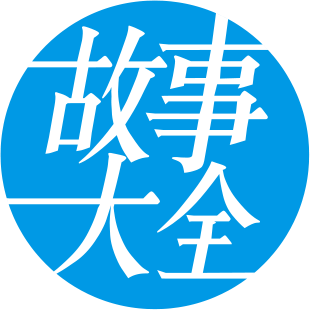谁做天子:新规则带来的大混乱
东汉中平六年夏四月丙辰,即公元189年5月13日,三十四岁的灵帝在他母亲——董皇后的寝宫——洛阳南宫嘉德殿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身旁只有一名宦官,时任小黄门之职的蹇硕从灵帝手中接过了遗诏。有关这份遗诏的内容,想必董后也已经了然于心了吧!

皇帝的母亲还是皇后,而不是太后,这未免有些不合常规,但却是事实。皇帝驾崩前,没有召集自己的大臣们,嘱托一下自己身后应注意的国家大政方针,这总是让人费解的事情吧!而灵帝生前又没有立太子,那份遗诏是否关涉新君继立,蹇硕没有及时公布,大家也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帝国不可一日无君,当务之急便是确定谁来登基。
按理说,这本该属于国家政治中的大事情。可是,从东汉和帝至灵帝的一百年间,却变公为私,成了纯粹的“家务事”,料理过这桩家务事的有三种人,他们是:
后宫的女主子——旧朝的皇后、新朝的太后。
女主子
出人头地建奇功
的父兄。作为外戚,他们通常在“家务事”中要扮演出谋划策的角色。因此,我们在史籍中就会看到,凡是记录有关新君继立的事情,就会出现一种固定的书法,即后与兄某某“定策禁中”,也就是说新皇帝的位子由谁来坐,这两种人就可以商量定了。此外,还有一种人,那就是宦官。百年间他们在新君继立上也出过面,那还是在安帝延光四年(125)十一月二日(公历12月14日)的时候,由中黄门孙程为首,十九名小宦官“聚谋于西钟下”,发誓改变阎太后和其兄长车骑将军阎显迎立外藩继统的计划,要把废太子刘保重新扶上皇位。十一月四日(公历12月16日)夜,孙程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斩杀数名大宦官后,控制局势,拥戴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阎《后汉书》(宋刻本)
显虽试图反扑,但终无所成。孙程等十九人因此举,皆封侯。
可见,皇帝的继立已经脱离开了法定的程序,甚至还要出现暴力夺权的事件,显然是不正常了。而百年间,走马灯似地换了十位皇帝,这十位皇帝继位时年龄都不大,最大的是桓帝,十五岁;最小的是和帝之子殇帝,还在襁褓中就被抱上了朝堂,供百官朝拜。
之所以如此,范晔在《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序》中说得就很明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所谓“皇统屡绝”,是说皇帝没有子嗣,也就没有了接班人。这从和帝开始就有了先兆,和帝十岁登基,
尝思鹪鹩尚存一枝,狡兔犹藏三窟,何况人乎 ----罗贯中
在位十六年,虽然有过很多皇子,但都早早地夭亡了,皇室自身无法找到病因所在,情急之下,索性把新生的皇子们寄养在民间,后来似乎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灵帝的皇子辩就是在一位有些法术的“史道人”家里长大的。而和帝直到驾崩前才勉强保住了一个百日大小的男婴,算是可以继统了。但婴儿还没到呀呀学语的时候,就告别了人世,和帝一脉自此断绝。不过,这并不是多么要紧的事情,毕竟皇族还很壮大,新皇帝可以从皇族成员中产生。要紧的是,选定新皇帝的太后和外戚迷恋上了幼主登基、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的模式,虽然他们会受到来自于制度层面的惯性干扰,尤其是东汉前期的当政者基于对前朝政治失误的自觉反思,明确规定了后族不得参与政治,使得他们在政治领域中一度还有所克制,像明帝时的马皇后尚能出面限制马氏兄弟的参政、封侯;和帝时外戚窦宪还需借尊崇太傅邓彪,变相地来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等。可是,太后、外戚一经控制了新君的继立,就完全可以确立天子对他们的依附,而天子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绝不能因为他年幼无知就可以被臣下否定的。手中有了天子这样的砝码,太后等人就没有必要去屈从于制度的摆布,而反过来就摇身一变成了皇权的代表,制度就可以为己所用了。
更需注意的是,太后临朝称制,却认为自己要和朝臣们在一起商议国家大计,是不成体统的事情,便让身边的宦官作了传声筒。宦官们一经有了这样的机会,摇身一变就成了现实皇权的代言人,正所谓“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序》),宦官专权又在所难免。
如果上述掌握着国家命脉的各色人等,处处为国家利益着想,能够让手中至高无上的皇权服务于政治清明,普惠子民百姓的话,出现另类的皇统继承模式,出现非士人的专权者,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历史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美好的幻想和真实的现实总有着很大的差距。
太后、外戚和宦官对东汉政治的介入,使得皇权发生了变异。变异后的皇权却是以侵蚀国家政治肌体为能事,把构成国家政治的要素,都看作是可以变卖的财产,甚至出现了三公九卿可以待价而沽的怪现象,并且产生了与之相配套的交易规则——“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这些人一旦品尝到了美食,穿上了锦衣,有着挥霍不完的金银,沉浸在“现实利益”的无穷“欢乐”中的时候,再让他们有所放弃,让他们用一个健康的成人的头脑思考思考为这个国家做一些执政者应该做的有益的事情,那可就是千难万难了。大将军梁冀因为听到了八岁的质帝说他是“跋扈将军”,敏感的神经就绷起来了,在他看来小皇帝认识是超前了,与年龄不符,对他构成了威胁。于是,就鸩杀了质帝,换个皇帝,让自己永葆富贵。这就是“贪孩童以久其政”。
任由私己利益的大肆膨胀,外戚和宦官的门生、故吏、姻亲、宾客充斥于国家政治机构的上上下下,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东汉末期有位很有才气的思想家仲长统,他在《昌言》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
政治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东汉帝国的崩溃看来是迟早的事情了。
而频繁的帝王更替也会使母后、外戚、宦官处于变化之中。新帝的确立就可能意味着新母后、新外戚、新宦官的出现,而旧集团一旦败亡,其所释放出的杀伤力极其巨大,往往会把国家政治推向解体的边缘,像桓帝诛杀梁冀及其宗亲,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
灵帝刘宏不是桓帝的儿子,其帝位的获得,也是太后和外戚商量定下来的,属于外藩继统。灵帝的母亲虽然能跟着儿子来到了京城,进了皇宫,但却没有资格做太后。灵帝在位二十一年,比起列祖列宗来,时间不能算不长了,他是否能够有所作为,遏制国家政治的颓势呢?虽然灵帝自我感觉不错,曾经问臣下说:“我和桓帝比起来,怎么样啊?”言下之意,灵帝认为自己要比桓帝强很多了,自然也希望臣下知趣,说些恭维的话。可是,被问及的大臣却不想昧着良心说话,但又不能让这位正在兴头上的皇帝丢了颜面,便对灵帝说:“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话中有话,不要比了,桓帝就够糟糕了,灵帝还不如桓帝。可以想见,灵帝一朝会是个什么样子。
而后世人一般也把东汉桓灵等同视之,认为那时是宦官专政,小人当道,上下离心,社会风气败坏,像曹丕在《典论》中说: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说: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84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出师表》(岳飞书)
但是在皇统继承上,较之前朝来说,灵帝应该算是幸运的,他有两个皇子活下来了。中平六年的时候,皇子辩十七岁(《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张璠《汉纪》说刘辩年十四。今从《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皇子协九岁。可是,麻烦也并未因此而减少。
灵帝是否顾及到了身后事,只要是蹇硕不把遗诏公布,那就是一个谜。这就使得何皇后成为当时最为心焦的人。子荣母贵,这对于后宫的妃嫔来说是一项不变的法则。况且做了太后,那是何等的美妙!但是何后之子辩在其父皇眼中却一直得不到宠爱。大概是因为他没有皇家子弟的那份雍容,平素的举止更多些世俗气。不过,作为嫡长子的他在灵帝驾崩之后继任大统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后总可以心安理得地等着做她的太后了吧!然而这里面却出现了波澜。
兴风作浪者是灵帝之母董后。这位颇有野心的后妃在其子当政之时,无法得到“太后”的尊号,但是她对于参与朝政却有着固执的追求,以致教会了自己的儿子怎样去卖官鬻爵,把皇宫中的西园变成了钱库。宦官成了“经纪人”。那时确定下来的卖价如果让他们的前辈看到,也只能自叹弗如了。新规按照秩级大小来额定“零售价”,定价标准是每石一万钱,你想做个郡守的话,就要拿出二千万。但这里面也有折扣优惠,条件是有德或是达到迁官年限,即“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像曹操的父亲曹嵩,据说就是向西园输钱一亿,才做了太尉。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三国历史频道,阅读更多三国故事/历史/人物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