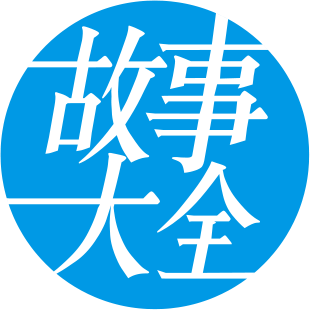父爱的枕头
后来,父亲和母亲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了。那年,我12岁,弟弟10岁。
离婚后,父亲不让母亲带走我们其中任何一个。母亲只好去外地打工,父亲留在家里照顾我和弟弟。自从母亲走后,我就对父亲有了深深的成见。
父亲作为男人,最擅长的不是吸烟喝酒,也不是打牌赌博,而是女人做的针线活儿。
我一直怪父亲心狠,让我们像飞离鸟巢的幼雀,失去了母爱的庇护。
母亲离开后的那些凄风苦雨的岁月中,父亲既当爹,又当妈,像一位慈爱的母亲照顾着我们。大多数时候,为了惩罚父亲,我和弟弟商量好了在外疯狂地玩耍,故意隔三岔五地把衣服和裤子的线缝扯脱。
我和弟弟都变成了调皮捣蛋的主儿,父亲虽然脾气很大,却从不批评打骂我们。那个时候,他忽然之间就学会了针线活儿。
最初,父亲那些蹩脚的针线活儿,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16岁那年的一个冬夜,我半夜醒来,发现父亲的屋子里还亮着灯。我就蹑手蹑脚地走近门边,透过缝隙,看见了令我终生难忘的情景。父亲坐在椅子上,正穿针走线为我缝补衣袖。
傍晚时分,我和弟弟比赛爬树,结果我把衣袖剐破了。晚饭时,我掖着藏着,生怕父亲知道骂我。睡觉前,我把衣服藏在枕头下。半夜起来,却找不到外衣了,只好穿着棉袄起来,却意外看见外衣在父亲手中。
如豆的灯光下,父亲的头微微地低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袖口,不紧不慢地穿一针,拉一下,再穿一针,再拉一下,一针又一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他全神贯注的样子,让我心生愧疚。
父亲在门里,我在门外,隔着一扇虚掩的门,我清楚地看见他缝补时笨拙的动作,像极了拐角耕地的老黄牛,慢腾腾的。再抬头看一眼,在那忽闪忽闪的灯光中,父亲脸上沧桑的皱纹,像小豆豆一样一跳一跳的格外显眼。

寒冷的冬夜,屋外冷风呼啸,哗啦啦地刮过屋顶,贴在窗户外的那层塑料纸,呼啦啦作响。父亲缝补一会儿,手指冻僵了。他捧着手,哈一口气,再继续缝补。
我站在门外,感到一股冷飕飕的风,从土墙的屋檐下鱼贯而入。浑身冷得直打寒战的我,心里却是倍感温暖。那是爱的阳光,穿透了童年的叛逆和幼稚,直抵被寒冷包围的心灵。爱的温度,融化了那块久居心扉的坚冰。
我想惩罚父亲的心理和那份坚硬的情感,一起融化在寒夜的温暖中。
那晚,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和心酸。感动的是从父亲那笨拙的缝补动作中折射出来的细心和爱心,心酸的是母亲不在身边的岁月,父亲粗犷的心思慢慢变得细腻了,体会到了他尽量不让我们受到委屈的心思。可惜,以前小小年纪并不理解父亲的苦楚,也不懂得父亲的疼爱,甚至看不出来父亲为了我们所做的改变。
我暗暗自责:对不起,父亲,我曾经对您有过深深的成见。
为了不让父亲尴尬,我悄悄地退回到里屋,躺在床上时,泪水还是忍不住溢了出来。
从此,我变了,弟弟也变了。我变得乖巧懂事了,弟弟变得不再调皮捣蛋了。
我们在父亲慈爱的阳光中,健康成长。
大学毕业那年,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不尽如人意,我得了失眠症。
父亲为我找了一些医生,我也吃了一些药物,均不见效。我依然夜夜失眠,白天头晕目眩。
那年秋天,父亲到很远的山上摘回很多金黄灿烂的银杏叶,一片片洗净灰尘,摊在门外的竹架上晒干,收藏。然后,他到镇上的商店买回很多橘子,把橘子一瓣瓣掰出来,用白糖腌制在瓦罐内,封存。
弟弟好奇,就问他腌制那么多橘瓤干啥。
父亲慢言慢语地说:“我要用橘子皮,那些橘瓤也不能糟蹋吧。腌制后啥时间想吃都可以。”
弟弟再问父亲:“你要橘皮有什么用?”
父亲一边忙碌着将晒干的橘子皮,用手细心地掰碎,一边回答说:“我要缝银杏陈皮枕头。”
弟弟疑惑地看着父亲。
父亲把掰碎的橘子皮和银杏叶一起,亲手缝制了一个枕头。当我抱着那个飘散着浓烈清香味的枕头时,百感交集。
我枕着父亲缝制的“银杏陈皮枕头”, 一如枕着一腔爱的暖流,安然入睡。
没过多久,我的失眠症就痊愈了。
搬家多次,我都没有舍得丢弃父亲缝制的枕头,枕头上面保留着父亲的指纹,以及爱的香味。
枕头上那些细细密密的针脚,就像一束束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没有母爱的天空,温暖着我失眠的神经,滋润着我忧伤的心灵。